版权所有:邱老文斋 地址: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
2008-2026 中网(zw78.com)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09031998号

笔会作品集949(姚增戗)
(郑东新区畅和街小学 姚增戗 专辑 11篇)
目 录
我的母亲
我奶奶最亲
绝户头三爷爷
奸诈的四爷爷
亲爷爷传记
大大伯大大的好
记二大伯
我佩服的能说会道的三大伯
过继出去的四大伯
一生受气的大伯母
三伯母老亲
我的母亲
以前在博客文章里曾经多次的写到我的母亲,有记叙文有诗歌,还有散文,包括现在好是对母亲的短暂而无私奉献的一生充满敬意和愧疚,当我敲打键盘的时候,不止一次的落泪,甚至是嚎啕大哭,为何提起母亲会有这种母子之深厚的感情,为何在很多时候又会忘记?
母亲属猴,1943年九月初九初生,1995年十月初六因白血病去世,在世间短暂的停留了五十二岁多27天,在这有限短暂的生命中,母亲养育了我们姊妹五个,伺候奶奶、爷爷、父亲,母亲是最无私的一个人,考虑自己几乎没有,吃的穿的都是最不好的,把仅有的好的吃的穿的给了我们,可以这样说,在家里是最无私的,母亲是亏死的吧。
我出生的第二年,我们搬家了,好奇怪,我现在还有印象,一岁半的孩子怎可能记得当时的情形?原来的老院子仅有二分半,孩子们多了我,就觉得住不下了,把老院子的房子拆掉了,盖起了三间大瓦房。
母亲在生产队是大老力,最高的工分8分,每次都带着架子车,出苦力再多挣三分。生产队更换了不知多少人队长,母亲都是受表扬的,只因为下力。走在去田地的路上,母亲也不忘遇到沟边的草,就去割一把,放到架子车下边的布兜里,回来可以喂羊,羊挤出奶,可以让家人充饥。路上遇到坑洼,还要挖两锨土来填平,为的是以后不再让架子车颠簸。
1984年,土地分开了,我家八口人(奶奶、爸爸、母亲和我们姊妹五个)分了十亩田,全靠母亲一个人在田间劳作,父亲还要进城务工抓钱,奶奶在家看孩子们,我们去地里帮忙也只有周日和暑假。可想而知,如果是现在我面对十亩田,能够有勇气和体力去伺候吗?母亲却耐着脾气,以一个农民的勤劳耕作着属于自己的田地,收获着属于家人的粮食,特别是栽水稻时节,晚上起稻苗,蚊子多,水还缺少,有时候干起,第二天拉到水田里把泥土涮掉。母亲站在一格格的水田里,望着绿油油的稻苗,充满希望的田野,面带笑容。弯下腰,一边插秧,一边移动身躯,一根绳子从一端移动到另一端。一看到我们放学来到田间,母亲更加有力量了,喜欢的不得了,好似救星一般,迅速的插完一格又一格,真的,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讲,插秧特别快,最后变成母亲晚上不在搭夜班,好好的休息,白天起稻苗,平地,下午放学大家一起栽稻,经过一夜的成长,稻子返青很快,比上午栽的成活率高。
等到我上班以后,大多数人加开始雇人栽稻,麦子有了收割机,稻子也可以机械化了。因为有了工资,我就不让母亲那么费力劳作了。或许是休息的缘故,进近六年时间,母亲没有下地干很重的活儿,竟然体力一天不如一天,后来牙龈出血,看了好多地方,吃了不少药,打了不少针,低烧一直不退,后来我骑着摩托带着母亲去肿瘤医院检查,第二天拿到结果,竟然是白血病,幼稚细胞达到百分之八十八,我突然感觉到天旋地转,暗无天日。
下午入住省人民医院,前后九天的时间,我一直在医院带了七天没有离开母亲,我深知这个病的厉害。周一来到学校升国旗,之后就有传呼响了,我回过去,是大姐的声音,那是不对劲的哭泣,我感觉到母亲的危险,等我到达医院,母亲已经断气了。我强忍泪水,叫了黄面的,二哥和我一起用大棉袄裹着母亲,背到了车上……。
办完母亲的丧事以后,我去医院清账,两万多元的医药费,当时的钱在我眼里就是纸,它救不了母亲的命,无论用什么都挽不回母亲,母亲的灵魂升天,母亲的笑容留在了我们心间,我们只能从相片上看到母亲的样子,只会在坟地里烧纸祭祀时哭泣,我们所能做的还能有什么?
我奶奶最亲
爷爷奶奶们早已不在人间,我的奶奶最后去世,1998年的三月初三,当我从梦中被父亲叫醒的时候,奶奶已经没有了心跳和呼吸,突然间我也晕倒了,重重的摔了一跤。
奶奶的一生可谓传奇,从小没有父亲。母亲拉扯着我奶奶和一个弟弟生活,奶奶的叔父没有结婚,一家四口就这样生活了三年,最后那个所谓的姥姥娘还是嫁人了,嫁到了黄河边,狼陈岗瓦坡村,后来奶奶去世了第二天卸孝是我带队去的。当时奶奶八岁了,说啥都不肯当带肚娃娃随母,于是和叔父一起相依为命。奶奶的叔父是一个厨师,在中牟县城老食堂做饭,少不了吃的喝的,奶奶也没有受罪。后来奶奶的叔父娶妻,但没有生子,只是抱养了一个儿子,如今的舅爷爷,一家伙拥有六个儿子,其中还有一对双胞胎,算是所有的家业都成了血脉以外的继承了。
奶奶家就住在中牟县衙门口,当时爷爷在中牟县当差,经人介绍就和奶奶结婚了,由于奶奶只身一人,没有了父亲,同时母亲远嫁他乡,所以和我爷爷感情甚好,1943年阴历四月,生下了我的父亲,奶奶一辈子就只有一个儿子,而我们是姊妹五个,这样的故事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命中注定,对于一个家族来讲,人越来越多。
当年的八月,日本人打到开封,从而通过中牟县来到郑县,这一路可把奶奶撵的没地方逃。奶奶的姥姥家是开封的,姨娘一个是开封的,一个是瓦坡的。当时父亲四个月大小,从开封姥姥娘家跑到中牟县找爷爷,又从中牟县跑到八岗,又逃到唐河,赶到彻底解散县政府,跑到郑县时,还是日本兵。好在日本兵对于小孩子还是诱惑的,奶奶和父亲没有受多大罪,逃过了一劫。
本来是富人的家,一解放变成了贫下中农,地没有一笼,房子充公大家集体合并,就连东大街西大街的两处四合院都没有去认领。奶奶的命运就这样随着郑州市解放而发生着变化,父亲从小赶上抗日战争,吃的不好,身体一直瘦弱,落下胃病,吃得少,并且一会儿就饿。奶奶是想尽办法亲我父亲,既使吃食堂饭,也要给父亲留一口馍。
奶奶当然不识字了,但是除了不识字,奶奶在衙门里见得多,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顺口溜都会说。奶奶让父亲进了学堂,从初小到完小,还是因为算术伤着了脑筋,不上了。就一个儿子独苗的奶奶当让心疼了,可是父亲的任性就终结了学习,回家务农一辈子。
奶奶就父亲一个儿子,爷爷在父亲26岁就去世了,家里奶奶说话是最厉害的,母亲打开始就惧怕奶奶的怪脾气,从来不和奶奶斗嘴,因为她知道,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,只有忍气吞声了,经历了近三十年,当我上班的时候,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,奶奶的怪脾气在我们姊妹几个的说服下才得以消减,母亲才当了掌柜的。
奶奶其实没有二心,就一个儿子,我们姊妹五个她都亲得不得了,那高兴劲儿甭提了,母亲只负责喂奶,都是奶奶把我们搂大的,甚至饿了的时候,还吃奶奶的乳房了,因此后来我们说瞎话,奶奶就打趣地说,你们小时候不少吃我的瞎妈,所以长大说瞎话。
最难忘的事要数小时候奶奶在家里照看我们五个,你可以想象得到,五个孩子,一个老人照看,其实是很累心很纠结的事情,都是亲生的,都可亲,几个人难免吵架打架,你猜奶奶是咋办的?吓唬我们,说你们再这样,我就去跳井了!离我们家不远,出门就看到一个大口的水井,我们都是从那里打水吃,我们也曾经去看过井,好深,好吓人,如果掉进去那会没命的。奶奶的话让我们胆战心惊,并且奶奶还做着要走的预备动作,大家就乖乖的老实了。后来我们逐渐长大了,和奶奶开玩笑,您去跳井吧!奶奶笑笑,并不作声。
奶奶八十四岁去世了,俗话说七十三,八十四,神仙不叫自己去,我回想了好多七人,大多是这样的年龄去世的,奶奶的去世也算是喜丧,大家并不感到多么的悲伤,只是离开了奶奶,心里还是些许的不舍。三月初三的那天晚上,下起了我有生以来的三月桃花雪,我是见证了如此的美景,奶奶惊天地泣鬼魂,不能说是巧合,更多的是奶奶奶的一生传奇色彩太浓了。第二天我随着一个表叔去狼陈岗报丧,这个表叔就是奶奶弟弟的儿子(建国),在我回来的路上,下起了大雨,我的新摩托车,竟然发动不起来,我就在路边停下来,跪在地上,祷告奶奶,是奶奶和我一起回老家了,一个她一辈子不愿意去的母亲改嫁的地方。我跨上摩托车,又发动了起来,走到郑汴路的时候,不知道往哪个方向了,可知道我是方向感极强的,一时间竟不知道东西南北,向右转就是郑州,我在自己心里嘀咕,果然走了五公里,看到了中某县的电视塔,我确信我找到了回家的路,等到回到家,我浑身湿透,皮衣皮裤皮棉鞋全部进水,为了奶奶,我义无反顾不后悔,我要对得起奶奶。
奶奶的祭日我时常记得,但是那一天往往因为村里边庙会忙碌,差一点忘记。怀念奶奶,有说不尽的话语,数不清的画面。奶奶下葬用的是最好的四五六的棺材(底是四厘米,侧面是五厘米,棺材盖是六厘米),比爷爷的一二三好多了。但是奶奶的身躯因为照看我们驼背了,放到棺材里还是驼背,只显得人短棺材长。奶奶的笑容长存,奶奶的影响极深。
我女儿见过她老奶,模糊的印象里,女儿看着相片说可吓人,我仔细看了看,也觉得挺吓人的,人老了,模样也变了,变得老了,吓人了。但老人的内心是慈祥的,对孩子们是真亲的。
绝户头三爷爷
在我的印象里,三爷爷是脾气最怪的,动不动就发脾气,没有人敢惹他,就连三奶奶也是害怕他一辈子。原因很简单,听母亲说过,三爷有六个女儿,没有儿子,在爷爷辈里,它被称为是唯一的绝户头,就是没有继承人的意思。
在我们老家农村,一直沿袭着无后为大不孝的习俗,一直以来,三爷爷都是闷闷不乐,都生了六个女儿了,还要生,可是三奶奶咋都不会怀孕了,就这样把四爷爷的三个儿子其中的老二过继给了三爷爷,就是我的四伯父,是四伯父为三爷爷和三奶奶养老送终的。
三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六岁,1976年,毛主席入土那一天夜里,三爷爷躺在床上,吃过饭便开始睡觉了,也没有人理会,其实是去世了。等到三奶奶喊他喝水不喝时,身体已经僵硬了,于是大呼小叫周围邻居亲人都摸黑来到三爷爷家里,我当时时跟着父亲一起去的。这话说来话长,我自小就是听话孩子,也喜欢和父母奶奶沟通,大多数时候他们出门总喜欢带着我,并且我出去是从不吃人家的东西的,既使长辈让吃,我也是坚持不能吃,说:我家有。
更不用说试穿人家的衣服鞋帽了。有一次就是去三爷爷家里,一个凉鞋三爷爷让我试试,是他外孙的,我连试也不试,我说我们不买,不是买不起,等我以后挣钱了再买,并且还给三爷爷买一双,当时三爷爷不知多高兴了。因此三爷爷去世了,我说啥也要去看看三爷爷。
三爷爷的院子门朝北临小路,西边是大路,路西是我们家的朝东大门,一路之隔的亲人,一生没有儿子的三爷爷,看我们特别的亲,我们哪有不去的道理。五天时间里每一顿饭都是小米,我记得很清楚,一口大锅,满满的焖小米饭,当时的菜只有白萝卜红萝卜,白菜还小,粉条倒是很多,红薯芡自己下的,吃起来筋道滑溜,一股股的好吃,我最喜欢粉条加瓜豆酱辣椒,拌着小米米饭稀糊浓。
出殡时,四伯父摔的佬盆,拉灵的都是本家的大老力,看到像父亲一样的孝子们,使劲拉着灵车,泪流满面,汗流浃背,那情形我只是在三爷爷的葬礼上见到过,以后就没有这样的节目了。因为三爷爷是没有儿子的绝户头,所以所有的孩子们孙子们都是他的亲人,用孝子拉灵的形式来宽慰他老人家。
三爷爷的六个女儿也过得十分幸福,好几个表姐表哥都是大学生,并且她们都有儿子,还不止一个,这也是遗传出生男女吗?迷信的说法打破了传统的观念,事实是自然规律,现在不也是男女要一个吗?按照国家的政策,做一个为国家奉献的人就中了。并且三爷爷的老幺还远嫁新疆哈密,那时候拍电报最快了,小姑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老家,第二天正好赶上三爷爷的葬礼,看到小姑姑高达魁梧的身材,黝黑的国字脸,短头发,那痛哭流涕,惊天动地的样子,恨不得把三爷爷给哭活过来,远离老家三十年,音信很少传回来,只知道他在哈密,老家没有人去过,更不知道详细信息,只有她们姊妹几个知道住址。那悲伤痛苦只有哭出来才代表语言的表达。
三爷爷去世后,留下三奶奶独自一人,守着偌大一个院子,里边很多枣树、石榴树,我们暑假里都喜欢去他家吃枣,后来九十五岁的以后的三奶奶开始糊涂了,已经认不得我们了,并且耳朵聋了,眼睛还好使,不管是谁他都骂,兔孙王八孙的胡说,我们趴到她耳朵上说才会听见,才让我们一起去吃枣,摘石榴。逢年过节,我们都会送去饺子菜角油条糖糕之类的,她老人家自己过,从不给我们端,收下后就没有回头碗了,为门就故意说,到时候我们来你家吃枣摘石榴中不中,她是满口答应,但是一到季节,就会出现骂人的事情。
老人都老矣,留下的只有回忆,如果她们能多骂几年,骂几句那该多好也。
奸诈的四爷爷
四爷在他们弟兄五个中去世的最晚了,我在老家上班教六年级数学时,他老人家可以说是自然死的,身体没有毛病,眼不聋耳不花,吃饭多,精神好,吸烟喝酒都不喜欢,典型的养生专家。
四爷得益于我爷爷的财富,由于我爷爷在中牟县和县长在一起做事,因此拿回来的钱大把大把雪亮的银子和金光闪闪元宝。奶奶和父亲也不在家,跟着爷爷在县衙生活,因此他们哥俩就算是没有分家,家里的一切都有四爷爷做主,当然作为最小的爷爷,也不喜欢当家,是金钱如粪土往老家送,让四爷爷帮忙照顾家里的父母,购买土地。解放前买地是老农民最喜欢的事情,整个铁路以西到邢屯以东,曾经全部是我们家的土地,地里的北瓜花生也曾经烂到地里卖不出去,太多了,还分给亲戚朋友一些。那里是一片上千亩的山岗薄地,麦子风一刮,麦根就会露出来,虽然收成不咋的,但是足可以富足一方了。
悲催的是四爷爷鼓动我爷爷在外边也买地,爷爷同意了,用三匹马拖回来银元元宝金锭,在四爷的老丈人家买了三千亩地,成片的树林,一眼望不到边,跟跑马圈地一般。我爷爷相信他四哥的话,从来都没有质疑过。
1943年,日本兵打到开封,爷爷和县长一家逃到八岗乡,随机就把家里的上千亩地给变卖了,这是周县长的主意,他们需要银子跑路,土地是带不走的,周县长曾经想过出国,的确,最后他们逃到过上海,一去杳无音信,爷爷和奶奶还有我父亲回老家当农民了。
当爷爷问起他四哥三千亩地的时候,四爷爷支支吾吾,说没事,每个月都有你吃的都中了,不用操心了。就这样,一家三口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到解放以后。
1950年,土地改革开始了,所有的老百姓都要划成份,看你家有多少土地,房子住的怎么样。结果我们家没有一寸土地,那三千亩写的都是四爷爷老丈人的名字,哈哈,因祸得福,舍去金钱土地,得到一个贫下中农的称呼,所有的以前跟着国民党周县长的事一笔勾销了,贫下中农嘛,啥都没有,一贫如洗,要是有钱有权家里会啥也没有?
四爷爷跟着受了连累,判定为地主,他家的房子住的是楼房,他是哥哥,我爷爷住的是山头留门的过街门楼。四爷爷曾经一度不理我爷爷,说是我爷爷害了他,到此我爷爷奶奶才知道他四哥的为人。
四爷爷即使当了地主,心情还是不错的,天天快乐自己。其实他老人家也很吝啬,中央票就是国名党的钞票,在他家的房子砖缝里塞了很多,这是后来拆迁房屋时,大家在外熟里生的土坯里找到的,五百的,一千的,五千的,可是那时候死也已经去世了,钱也不当钱花了,甚至是一文不值。
四爷的一生曾经是幸福的,虽然为人不是很厚道,但知道养生之道,活的岁数最大,死得最晚,钱财最多,三儿四女,也是一种活法。
亲爷爷传记
定下这个题目其实很别扭的,好似那些爷爷不是爷爷,老幺是我亲爷爷,父亲的父亲,总觉得有点那个,但我们村的习俗就是这样,叫爷爷的不一定是亲孙子,好似一种称呼不可言喻。
村里也有好多人称呼老五爷的,我的伯父们称呼我爷爷叫老瘩,老疙瘩,最小的意思吧。
我爷爷他们弟兄五个,姊妹八个,比五男二女的说法还优秀,三个姑奶奶最后都分开亲戚了,我印象中是和最小的姑奶奶亲戚,文化路大铺村的,她老人家最特别的是右手发抖,后来知道了是帕金森,和邓小平主席是一样的病,小时候还学着她抖手了,不知被父亲骂过几次?并且她还结巴,串亲戚时也跟着学了,结果后来说话也有一点口吃。
在他们弟兄里年龄小,辈分高。我的父亲比我大伯家的堂哥大三岁,我老弟和堂哥家的二儿子一样大,堂哥家的大女儿跟我一样大,经常被叫做没尾巴叔(老鼠),没胡爷。
爷爷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:由于是老幺,所以没有上过一天学,为什么?因为前几个哥哥都没有成才,所以老幺就放弃了。不过爷爷个子最高,身体魁梧,从小喜欢舞枪弄棒,勇争好斗,练就一身武艺,也曾经去少林寺拜师学艺三年,回来之后经爷爷介绍,去了中牟县县衙当了保镖。当时县长是我们一个村的周姓富族,好多人都在那里跟班,有当师爷的,有当教头的,反正听说多半人都沾光了。
爷爷当然也不知道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,有口饭吃,凭力气干活而已。保护县长就是他的第一要务,为县长办事就是他的工作每每说起这事我都很激动,也要的身手那叫中原一绝,曾经在河南擂台坚持三天,睡觉合衣,连战靴都不带脱掉的,骑上大白马叱咤风云,南北二京来回不消几日,盒子枪不说是百发百中,弹无虚发,百步穿杨真有此事,奶奶和家族的人曾经在麦场里见证过。
为了保护周县长及其家眷逃往唐河县,被追杀的日本兵差一点打死,子弹就从高礼帽帽檐飞过,把帽子都打飞了,爷爷机智的像电视里演的一样,飞身起右腿,左脚跨蹬,与大白马平行,十颗子弹射的日本兵人仰马翻,不再追赶。这段神奇的佳话,被我们村的人流传至今。
回忆起爷爷真带劲,有好多的故事充满了我的思绪,好似一下子把我带到了解放前,爷爷的榜样精神,那股拼搏的精神,不怕死的勇气,忠肝义胆的侠气,都是我反思时候命题。
爷爷一生是短暂的,六十多岁就去世了,比起那几个爷爷活到九十多岁,不论享福受罪,都无怨无悔。在他们弟兄五个当中,他是最有本事的,挣钱最多的。把爷爷父亲居住的大门楼修的在东郊是最好的,三层的挑檐大门楼,黑漆金字的牌匾,朱红的大门,虎头的门栓,两边两尊大石狮子,来此乘凉的邻居无不羡慕爷爷的孝心和本事。在爷爷父亲去世的时候,爷爷弟兄五个孝子拉灵,上好的樟木棺材,桐油里外浇了三遍,在2006年清明那天,因为郑东新区的建设,修东风南路,我们的坟地需要拆迁,起坟的时候,棺材还没有腐朽透,所有的亲人都见证了这个事实。
可是当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,我父亲26岁,家里一贫如洗,差点儿用高粱杆卷着下葬,还是大伯父张罗着,借生产队的钱,喝了一口123的棺材(棺材底是一厘米厚,侧面是两厘米厚,上盖是三厘米厚)。父亲说过,五年之后才把钱还清,当时真的是家无分文,所有的费用都是借的。
曾经富甲一方,跑马圈地,整麻袋银元,元宝,金条,拥有几千亩地,在中牟县耀武扬威,数不清多少宅院,就连郑县东大街西大街都有几个四合院的爷爷,只因日本人来了,全国解放了,失去了工作,回家当老百姓,一贫如洗的度完了余生。也是在那次起坟的时候,爷爷的钢板底战靴还有锈迹斑斑的模样。
回忆起爷爷,无数的感慨,无数的无奈,如果爷爷能够活到现在,无数的奇迹将会发生,如果没有如果,事实就是这样。我也曾经参加过无数的婚礼和无数的葬礼,人生悲欢离合,无论男女老少,活好当下最好!
大大伯大大的好
四爷的大儿子年龄最大,因此在我们本家,他是掌门人。四爷有三个儿子,爷爷弟兄五人,子嗣一共七个,三爷无子。
大大伯生性脾气古怪,不喜欢与人交往,四爷家也是有钱的地主阶级,因此大大伯也上过私塾,就是不吭声,老鳖筋,教书先生打手板他也受罪了,可是敲他的脑袋时,大大伯骂了一句:瞧你爷爷的头弄啥了。也是因此辍学了,人家不教他了,只好回家学习木匠。
大伯伯拜老师还是一段传奇:四爷爷家有钱(都是我爷爷从中牟县带回来的),找到了我们村最好的周姓木匠,可是人家老木匠不买账,去了一次人家不收徒弟了,又托人说说收个关门弟子吧,人家还是不答应,回应一句话:我不是孙子!我更当不了爷爷的师傅。没办法,大大伯自己自学,说来也是,自学的木匠一点儿都不比那个周老师的徒弟们差。
大大伯个子高,力气大,抡起斧头赛铁牛,伐木三下五去二,拉锯一个人不跑墨线,刨平面光滑无痕,凿眼方方正正,开隼角度恰巧准确,不管是打梁,冲椽,锛檩条,制作门窗,在我们村都是吃香的木匠。并且和周姓老师的大徒弟“三群”成了好朋友,俩人一起干活,为乡里乡亲家里不知道干了多少参忙活儿,从来都不带拿人家钱的,大大伯这一点儿在老家落下的美名流传广矣!
特别是那些老人,都希望见到我大大伯,想和他攀谈几句,说说好话,那意思就是在百年之后大棉袄的事,给他合一个响当当的棺材。大伯伯当然知道这个事情对于老人是多么的重要啊,就连我爷爷去世,都是大大伯张罗的棺材。
大大伯不信迷信,从来不烧香拜佛,他说手艺就是你吃饭的家伙,只要认真去做,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中了。也正是这样,大大伯一生都是光明磊落的,靠自己的力气和手艺度过了七十岁的人生。
大大伯去世还是因为木匠活儿,买了一棵树,需要连根拉走,就在那颗树倒下的一刹那,把大大伯狠狠地摔了一下,没有拉到医院就去世了,也是他们堂兄弟七个中去世最早的。
想起大大伯与四爷爷不同的性格和为人,你能说父子会遗传?做人也会影响吗?相信大大伯在那边会心安理得的继续自己的生命。
记二大伯
二大伯在我们家族里个子最高,还有一点驼背,因此外号“骆驼”,我们家好像好多人都有一点驼背,我也是,站不直,腰椎的问题吧。
二大伯是我大爷爷的唯一儿子,取名宝田,他们是田字辈,因此也称小名‘宝宝’,我们乡村发音就变成了“包包”。由于好多父老乡亲都叫他“包包”,小孩子们饿了的时候,就会说想吃包包,大人就会故意的说去你二大伯家吃吧,他家有个大‘包包’。
二大伯一生一个女儿,六个儿子,夭折一个大的儿子,和大爷爷相比,好像是翻转了。大女儿名字叫‘小妮’,嫁到离我们家三公里远的二十铺村,虽说不富有,但也比二大伯伯家里强。
二大伯由于大爷爷的贫下中农底子,解放以后便当上了生产队长,根正苗红,无产阶级专政的舞台让二大伯发挥了政治魅力。甚至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,二大伯还当上了大队革委会的领导,在三里五村都是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的革命头目,用他的回忆话说:那时候做了不少恶。其实都是乡里乡亲,没有必要下手那么狠,只是政策到了那一步,上边要求那么做。
说起浮夸风,二大伯法子真的挺多的,书本上介绍的虚报产量,检查弄虚作假,他都干过。麦场里,一囤囤的麦子连边扯沿,丰收的景象就在眼前,你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可是你不知道里边都是麦秸秆,上边一层麦子。等到检查麦秸粪堆时,里边是木棍檩条支撑着,周围是虚虚的麦秸粪和黑泥糊糊,粪堆周围是人手一辆架子车、铁锨、粪叉、挑水的扁担水桶,茎篮,其实大部分都是邻村借的,检查完之后急溜咣当就会从小路悄悄地送过去,以便于人家应付检查,老百姓会互相帮助的。
可是联产生产承包到户之后,也就是取消了大锅饭,每家每户都分到了责任田,二大伯不当什么领导了,年龄也大了,退居三线了,在家里领着孩子们干地里的活。农闲的时候带着孩子们推石磨,磨豆腐。挖个坑,坐上一口大铁锅,,周围用木棍架起来一盘石磨,用绳子绑上一根缘石磨切线的白蜡杆,黄豆泡上一夜,下午就开始捞出来,倒在石磨上边的窟窿上边,随着弟兄几个慢慢的推动石磨,黄豆被碾压的希糊浓,豆浆随着石磨下盘外立面的沟痕逐渐的流到下边的大铁锅里,孩子们看到这情形,推得更欢了,我曾经也好多次的去推石磨,亲眼看到这原始的磨豆腐的情形。
等到豆浆完工后,开始用棉布做的包单过滤豆渣子,分离做豆腐的豆浆和豆腐渣。刚开始的时候,我们也吃过豆腐渣,用大葱炒着吃,可是后来实在是难以下咽,没有人吃了,只有喂猪了。
下一步就是点火煮豆浆,开火之前,二大伯总是祷告几句,不知说的什么,估计是让豆腐成功之类的。待煮沸之后,开始加入卤水,这可是技术活,泡多少豆,豆浆到锅沿什么位置,下多少卤水,二大伯心中有数,从没有告诉过我们,只是在他干不动的时候,告诉了本家堂哥二哥,也就是我在上班路上遇到的二哥泪两行的清洁工。
捞出来的凝固的豆浆,捯进豆腐模子里,用石头重重的压上三个小时,完美的豆腐就开始凉起来了,第二天,二大伯用架子车拉着两格豆腐走街串巷,吆喝着:“谁割豆腐”“谁换豆腐”。基本上晌午十分就到家了,换到大豆可以继续泡豆磨豆腐,换到大米小麦就需要变卖成现金,购买大豆了,一般很少得到钱币的。
我们没有嫌二大伯抠酸,虽然我们很少吃他的豆腐,豆腐渣吃过,豆浆糊到锅底的锅巴吃过,那是觉得都是挺好吃的,现在回忆起来也是味道蛮好的。
我佩服的能说会道的三大伯
三伯父是智慧老人,老好人,懂得说话艺术的人,能把三国说的不反,东郊难得的领导,也是我唯一一个佩服的人,并且单独为他老人家写了悼词。
在以往的博文里好多次提到三伯父了,这里全面的回忆记录过往,还是一种缘分,以示对他老人家的尊重。
三伯父是二爷爷的大儿子,由于二爷爷读书不开窍,因此,三伯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,从完小到初小,再到中专,是我们村走出去最早的干部。
三伯父参加工作在解放以后,所以退休之后就是退休干部,非离休。很可惜啊,他老人家是1950年参加工作的,1930年出生,二十岁在郊区供销社上班。
三伯父在供销社工作了一辈子,见证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全过程,退休之后无不感慨,社会的变革,供销社有特权单位到发不出工资,由吃香单位到没有人理的负担单位,甚至好多人上访,三伯父退休之后不止一次的结伙去上访,好多问题积压着都解决不了,原来能说会道的老干部也解决不了问题,如果是上班期间,那没有三大伯解决不了的问题。
还是说说三大伯在供销社上班时的辉煌吧。解放了,物资匮乏,三大伯在郊区供销社上班了,郑州市和全国一样相应的成立各级供销社,为的是计划经济下,保障供给,稳定物价。三伯父从售货员干起,由于能说会道,脑子管用,很快就从须水公社小李庄村代销点调整到须水公社供销社售货。须水离我们老家近三十公里,三大伯吃住都在那里,除非是家里有事,从来都没有回过家,以至于很晚才找到老婆,很晚才生下第一个孩子。这都是工作人员的写照,一般在老家的男人早早的结婚生子,而上班的往往比人家晚八到十年。
那时候也实行人员流动,不让你在一个地方工作,三五年就调整一回,因此祭城附近乡村三大伯是走遍了,也结下好多的朋友。对了,三大伯一般不喝酒,酒量不行,很少抽烟,也许是工作人员穷的写照吧。
对于有需要帮助的人,无论是不是认识,三大伯都是热心帮助,他会把卖点心剩下的白糖碎末收集起来,谁需要白糖了,又没有糖票,是喂自家孩子的,那都派上用场了。谁家孩子大了,需要自行车上学上班,他会想办法弄到自行车票,平价买一辆给您家送去,而三伯父一辈子就骑了一辆二八的大破驴,我也曾经问过他,不是自己吝啬,而是找自己的人太多了,需要自行车票没法办,只好把自己的票给了大家。
由于三大伯名声好,能说会道,因此乡亲们家如果有婚丧嫁娶,需要说和的都找他。好在后来调整到了老家附近,每逢周日,都是三伯父出门的光荣任务,人家不吸烟,不喝酒,就能把事情搞定,包括我们姊妹五个的婚事送好结婚,都是三大伯一手操办的,你能不感激这样的大伯吗?
1989年秋月,三大伯光荣退休了,我也开始上班了,三大伯曾经给我说过,你要好好工作,将来接我的班。这压力我也曾经试过,但是退缩了,你需要拿出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做,我一个老师耽误不起,也不能老请假啊,再者说了,由他老人家去办,我还操什么心啊。
不幸的是2013年,八十四岁的老人经不起时光的摩挲,闭上眼睛,撒手人间。没有人不伤心落泪,老父亲曾对我说,你三大伯走了,我心里难受,自小跟着你三大伯一起玩耍,如今再也叫不醒了,人活着还有啥意思,想想早晚都要闭眼,泄气啊!
对于亲人,三大伯亲得很,对于路人三大伯朋友相待,一生只做一件事——好事,一辈子做了一辈子的好人,为孩子们留下的是数不清的正能量,缅怀三大伯让我告诉自己,接过老人家的接力棒,为老家人办点儿好事,让他老人家的灵魂得以安息。
过继出去的四大伯
四大伯是四爷爷的二儿子,从小过继给了三爷爷,老两口也是像亲生儿子一样看待,结婚娶妻,照看孙子孙女(四大伯三个儿子,一个女儿),二老去世的时候,都是四大伯给摔的佬盆儿,也算是养老送终了。
四大伯生性耿直,一根筋,说一不二,在他的内心世界,我隐约感觉到总是不舒服的,自己过继给别人,亲生父母却不能尽孝,有病的内心比身体的折磨更让人不安。四爷爷去世,四奶奶去世,都没有让他出一分钱,家人的歧视更让四大伯仇恨无比,到后来,他们弟兄三个都闹得不说话了,彼此都看不起对方。
这些伤心事提起来就是一种悲哀,自己没有儿子,非要过继一个,自己的家产宅基地会有多少价值啊,非得有人继承?造成的心理扭曲他们是不知道的,传统迷信坑爹。
在我的记忆里,四大伯不会什么手艺,但是力气大,会干农活,吃得多,在生产队挣工分最多,三个儿子也早早的参加劳动,因此他们家的大老力每到年底都分到好多粮食和现金,在那个年代他们可以说是富裕一些,我们是邻居,时不时地去他家借一碗小麦面粉,四大伯每逢看到我端着一个洋瓷碗,就笑嘻嘻的说,老三又来了,让你大娘给挖一碗面回去吧,给你妈说,不用还了。这熟悉的话语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,我当时就纳闷,我们家人也不少,为啥老借四大伯的?回去问了奶奶,奶奶说需要我们长大去队里干活挣工分,就会有白面吃,所以二哥就早早的不上学了,十六岁开始拉架子车挣工分了。
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了,地里需要很多粪,四大伯就拉起架子车,到城里寻找垃圾,说来也巧,憨厚老实的四大伯竟然和郑州市变压器厂挂上了钩,天天都去拉。弄得地肥谷满仓,还是富裕的生活。我曾经和四大伯一起去过变压器厂,模糊的印象应该是在人民路和商城路东南角,很大的一个场子,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倒闭了,修建了加油站,再后来加油站爆炸一回,拆掉了,建成了现在的“百盛”。
四大伯也不会吸烟,更不能喝酒,也许是吝啬的缘故?包括他的三个儿子也是这样。一个字不识丁的老人,把子女都养大成人,结婚生子,延续着上一辈的生活,一位普通的老人,忍受着巨大的过继压力度过一生,幸运的是,四大伯在征地拆迁时也得到了补偿,分到了房子,过上了单元房的幸福日子,为子孙留下的不仅仅是房产财富,更多的是老实为人。
一生受气的大伯母
大伯母名唤宋大妞,祭城村人,非富即贵,个子不高,患有老病,除了睡觉,平时都会从胃里冒出一股气体,通过口腔排出,不是普通的打嗝,那就是病,也没有看过,在农村就是这样,一直带到坟墓了。
大伯母生性直来直去,说话跟撩砖头似得,不知道砸住了多少人,人家不以为然,习惯了噘嘴丧脸,人人跟欠了她二斤黑豆儿,非极凶相,难以靠近。
大伯母生育四个儿子,两个女儿,差一个就是五男二女的好命,就这也不错,一步之遥了。听奶奶说过,本来还有一个儿子,早早的夭折了,不与外人道也,这就是命。
大伯母当儿媳妇相当受罪,虽说在家里是大女儿,娇生惯养,又有公社所在地的优势,嫁到我们金庄村,四奶奶也不是瓤茬,使唤大伯母一套一套的,大伯母可是受了老气了。家务活都要干,地里活也要干,生孩子不到满月就要下地挣工分,拉架子车。不过大伯母虽然个子低,善有力,挫是挫,善砸馍,也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躯。地主女儿嫁地主少爷,解放前是门当户对,有丫鬟仆人长工短工可以使唤,日子好美,但是解放之后就成了上边说的样子了。
等到大伯母娶上大儿媳妇之后,四奶奶还健在,大伯母像婆婆一样使唤儿媳妇,可是儿媳妇有文化,哪里听她一个个子低头发稀,一看就像草上飞婆婆的横行!时不时的用一用柔招,到四奶奶那里说自己怀孕了,晚上没有休息好,所有的事情还需要大伯母干,弄得里外不是人,当儿媳妇一辈子受气,当婆婆时儿媳妇都没有把她放到眼里,这也是解放前后妇女的真实写照,不是她自己,村上的很多妇女都是这样的尴尬处境,一辈子都没有翻身。
大伯母去世的丧事我都有参与,三大伯手把手的教我,办丧事的流程,七天之后丧葬,都需要干哪些事情,找哪些人,怎么算五七,如何浇七,单七女儿上坟,双七子孙儿媳祭拜,白天就把家里的烧纸儿全部清理到坟地烧光。以前有下葬第二天去外婆家(姥娘)卸孝,挨家挨户磕头之后,就把孝衣孝帽脱下来了,好繁琐的事情,一点都不敢马虎,因为自己是办事的,出了纰漏那可要丢人了。
三伯母老亲
三伯母在我印象中是一个驼背,需要仰着脸才能和别人对话,说话声音沙哑,好似几多委屈,总是说不出的哭诉。
三伯母经常来我们家串门,老看我奶奶,他们年龄相近,或许是同病相怜,或许是几分相似,我奶奶也是驼背至极,两个人唠嗑会到很投机的时候哈哈大笑,好似两个疯老婆子。
三伯母生有两二儿子,三个女儿,都是不爱学习的料,三伯母也不识字,孩子们都上学了,可是都没有上大学,都在家务农,或娶妻生子,或远嫁他人。
三伯母的头发白得很早,我曾经问奶奶,奶奶说是少白头,轮到六十多岁的时候,头发又开始发黑了,真到去世的那一刻,满头乌发,恰似返老还童一般,。这样的反常现象我无从解释,乡亲们也极少见到,说啥的都有。
每逢过年过节,三伯母总是做上好吃的,端到我们家,先给我奶奶尝一尝。三伯父在供销社干事,虽不算富裕,但总有肉、面、鸡蛋、糖之类的特供品。进门头一句就是:“老婶,尝尝吧,头一锅,头一碗,您先吃!”这种尊老的话语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,每每想起这句印象深刻的话,我都感觉到了农村人那种淳朴的孝敬之心,也让所有的家人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了乡亲们的浓浓深情厚谊。
小时候在三伯母家玩耍,她家的大黑狗是散养的,从没有用绳子或者链子拴过,和到家的人和睦相处,那一天我捞着大老黑的尾巴在转悠,突然间大老黑转过头,狠狠地咬住了我的右手大拇指,三伯母很快拿出来一团面,,糊在了我的右手拇指上,她告诉我,到家也不要去掉面,吃一顿饭后就可以去掉了,只要不流血,就会结疤,慢慢就好了。果然是这样,慢慢的就好了,现在还能够看出来留下的疤痕,一个狗牙印。那时候也没有狂犬病一说,如果是现在真的需要打针吃药。
大概是我上初中的时候,和三伯母家的小女儿是同学,经常一起学习,是一个学习小组的,还在她家吃过饭,记得一颗葡萄树在暑假结束后才红,三伯母剪下好多,让我用上衣兜着拿到家,这是多么的亲啊,可是我的衣服被染色了,再也穿不出去了。回头奶奶告诉了三伯母,三伯母哈哈大笑,一个没有上过学的文盲,生活中只知道亲的她哪里知道会出现这种事情,非要赔我一个短袖衫不可。
回忆起三伯母,满满的谢意在流淌,我遇到的好人在我的记忆力好多好多,受他们的影响好大好大。如今这样的妇女很难遇到,奸诈,自私,自己就是太阳的人比比皆是,缺失了自然的道德标准,拥有了先进的文化,产生好多不谐和的砝码,以至于发生了好多不愉快的事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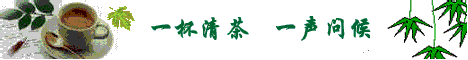
 最新评论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