版权所有:邱老文斋 地址: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
2008-2026 中网(zw78.com)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09031998号

笔会作品集953(田百合)
(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一中 田百合 专辑 8篇)
目 录
父亲的百宝箱
父亲的园子
父亲的纸笸箩
父亲的旱烟叶
父亲的缝纫机
父亲的小发明
磁性的爱
白雪铺路,为姨妈送行!
父亲的百宝箱
时常想起父亲的那只黑色木箱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那只箱子就像百宝箱,装满了神秘。
从我记事开始,那只箱子一直是锁着的。说锁着,也不确切,因为只有一把很旧的锁挂在上面,锁是开着的。但是,除了父亲本人,别人是不能随便打开的。箱子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,一直都是个谜,直到父亲去世。
那是一只黑色带底座的长方体木箱,外观没什么特别。倒是底座上一对对开的拉门很打眼——拉门的木框上镶嵌着两块瓷雕(我不知道这样描述对不对),但那确实是表面有凸起花饰的、约有A4纸大小的瓷制的板块,瓷质细腻,颜色纯正。淡雅的湖蓝色背景,衬托着粉红色的荷花和绿色荷叶。花叶间还有鱼儿游动。花朵、叶子、鱼儿都是凸出来的,栩栩如生。小时候,我特别喜欢摸那上面的鱼儿,好像可以一把抓下来。箱体和底座都是实木的,但具体是什么木质,我就不知道了。
听母亲说,箱子是土改时分得的“胜利果实”,原本应该是一对,另外一只不知分到了谁家。
如今回想起来,那箱子底座拉门上的瓷雕,或许能算文物吧?但那时父母也只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盛物器皿,以至后来不知被谁不小心打碎,换上了旧纸壳。
从我记事起,那只箱子就只属于父亲。父亲经常会打开箱子,取出或放进物件。比如晚上临睡前,从里面拿出一本书读;或者在什么特别的日子,从里面掏出几颗糖块或带有辣味(存放久了造成的)的花生粘、糖姜片分给我们。
至于放进了什么,我们都不曾在意。
所以,父亲的箱子里,到底都有些什么,我们并不清楚。父亲是个非常仔细的人,他放置物品总是很有规则,分门别类,摆放整齐,仿佛做了防伪记号。曾有几次,哥哥们偷偷翻他的箱子,都被他发现了。大概是哥哥们发现箱子里其实没什么好吃好玩的,或者怕父亲发现训诫,以后也就不翻了。
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天,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,大家一起把目光聚集到了那只箱子上。我知道父亲不会有一分钱的存款,也不会有一件值钱的古董(文革时几次被抄家,连书籍都被烧毁了,即便有古董,怕也早被抄去),他一辈子最大的财富就是十个儿女。但那只塞得满满的箱子,又着实让人好奇。
母亲坐在炕上,让人将父亲箱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,摆在面前。我们围站在炕沿边,期待着揭开百宝箱里的秘密。
当箱子空空如也的时候,大家都缄默了。良久,母亲发出一声低低的哀怨:“唉!这就是你整天藏着掖着的宝贝?明天都给你烧了带去,留下也没人稀罕!”
继而,人群中有人抽泣起来。
堆在母亲面前的物品,可谓琳琅满目:成摞的纸色发黄但包着书皮的书籍、成捆的保存完好或边缘已破损的小人书、成打的彩色皱纹纸(谁家老人去世,请父亲给做祭品纸活用的)、成套的水彩画用料、象棋和棋盘、半瓶糖姜片、一个厚厚的本夹子,还有两样让人哭笑不得的东西:一捆塑料袋和一捆烟标。塑料袋有透明的、不透明的、大的、小的,甚至还有装方便面用的。都是开口剪得齐整并使用过的,一律叠得平平整整,用一条细绳捆扎着。烟标有软质的,也有硬纸壳的。最早的烟标是蓝色花底的“迎春”。同样被叠得整齐、捆扎得有棱有角。我知道,那些塑料袋,绝非父亲自己食用过的食品袋;那些烟标,也绝非父亲自己吸烟留下的。他之所以收集、收藏那些东西,我猜想有两个目的:塑料袋是为了自家装物品使用(那年代方便袋可不像现在这样泛滥),至于烟标,也许是父亲的一个爱好,也许是为了给人家做纸活时派上用场,能节省点。
我翻开那个厚厚的本夹子——那是一本记账本。何年何月何原因借过何人多少钱,何年何月何时何地由谁归还了人家;何年何月因何收入了多少,何年何月为何花费了多少,甚至买一斤盐、一包火柴,都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。翻到最后,我发现截止父亲去世前一年,我家已不欠外债……
原来,父亲的百宝箱里没有一件宝贝。但我觉得它装满了财富,到现在,我还从里面不断地汲取着。
父亲的园子
从我十一、二岁一直到二十五六岁,我家园子的格局基本是这样的:
窗前一个土坯垒起来的花台子,里面是父亲播种的多样花草,都不怎么名贵。什么鸡冠子花、步步登高、佛顶珠等等。当年还不知道有些花的名字,后来看电视和网上图片说明才知道的。比如被父亲叫做扫帚梅的,其学名是波斯菊;再比如被父亲叫做大黄花的,学名是万寿菊。
花台子西侧靠近栅栏的地方,是两簇特别的花。一簇光长叶子不开花,叶子宽大状似马蹄,植株不高,是独角莲。每年秋季叶子落尽,父亲会亲手把它形似马铃薯的根茎挖出,装进一个很大的木箱子,用半湿的土培好。第二年春天,取出几颗载入花台子西侧靠近栅栏的坑里,余下的就晾晒、收藏起来了。另一簇,是西番莲,也叫天竺牡丹或大丽菊。植株高大,花朵艳丽,招人喜爱。它虽然开花,种子却和独角莲一样,是根茎的。
父亲种这些花花草草,可没少挨母亲埋怨。母亲觉得那些地方种菜更解决肚子的问题,种花又不能当饭吃,真是太浪费了。其实,父亲种花也不完全是为了观赏。独角莲和鸡冠花、万寿菊都是中药材,特别是独角莲,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起了不小的作用。父亲用独角莲根块熬水、将独角莲的根块捣碎做药膏,治愈了母亲的乳腺炎;用鸡冠花的花冠加红糖煮水,为亲戚治痛经;教我用佛顶珠花的花瓣染指甲,等等。我以前不明白父亲为何会懂那么多药理,这两年听三姑妈讲家史,说大伯年轻时学医,后来自己开了药铺诊所,解放后曾做过辽宁大虎山医院的院长。父亲当年大概受过大伯影响吧,我想。
这些花草的南面,是种各种蔬菜瓜果的地方。开春时,早早被父亲修理成规格统一、平坦齐整的菜畦。修整菜畦时,父亲像个工程师,埋桩钉线,横竖、高低、宽窄,都有严格的要求,丝毫不能差。所以,我家的菜畦初时,就像用格尺画在大白纸上的图样,规整漂亮。直到那些豆角、黄瓜秧拉出翠翠的蔓子,被秫秸架起来,那些规整的格子才慢慢被遮盖起来。
父亲种菜舍得施肥、浇水。韭菜、豆角、黄瓜、茄子、辣椒,这些家常菜应有尽有。各种菜刚下来时少,等到了旺季,自己吃不完还要给邻里乡亲送点。
房前的园子比较丰富,房后的园子可就简单多了。从滴水檐下的一条小沟向北到院墙,南北十几米长、东西六七间房子宽的地方,是后园子。后园子通常只有两种植物:玉米和旱烟。因为父母都抽烟,大哥、二姐、二哥等长大了也抽,左邻右舍的亲戚朋友们来了也得抽烟。所以,旱烟叶在我家的需求量可不少,要拿出后园子的三分之二种旱烟才够呢。
种旱烟是个苦差事。从比小米粒还小的旱烟籽发芽到两尺长的旱烟叶香薰、捆扎、晾晒再到可以吸,一连串繁琐的工序真是累死人。种旱烟之前,母亲先要把烟籽儿放进一个用棉袜装缝成的小口袋里,然后在温水里浸泡一下,捞出后放进大瓷碗里,上面盖上湿毛巾等物,将大瓷碗放在温暖的地方,比如炕头。以后,每天三次给大瓷碗洒水、投换湿毛巾,以保证烟籽的湿度。三五天后,烟籽发芽了,白白的芽芽挤破黑黑的烟籽壳,让人看了倍受鼓舞。这时,父亲早已把种旱烟的地翻好、打垄,还在垄沟里铺上了一层白眼沙(从白沙坨子上取回的没有任何杂质的沙土),这就是旱烟幼苗的温床了。等到父母把发了芽的烟籽撒下去,再敷上白眼沙踩实(俗称踩旱烟),我们兄妹的任务也就开始了。每天早晚两次,用父亲自制的喷水壶往垄沟里浇水。起初,垄沟里只有白白的沙土。三四天后,才隐约看到针尖一样细小的白芽芽拱出来,那就是烟苗了。烟苗小时候可娇气了,它对温度、湿度的要求都很高。浇水多了,就冲跑了;浇水少了,就干死了。烟苗还喜欢“偎窝子”,你看着它出来了,以为它很快就长大了吧?其实它可懒呢,十天八天都不肯长高一毫米。这段时间,我们几兄妹要有很好的耐性,按时浇水。哥哥们负责挑水,我负责喷洒。每次浇完烟苗,鞋子和裤腿都得湿,后来干脆就光着脚丫挽起裤子。烟苗长到四个叶子的时候,我们浇水的事就少了,父母要做的事就多起来了。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,逐个给烟苗掐尖打杈,除底叶。保留到合适数量的叶子后,就不让它们再多长了,以确保烟叶“上烟”。最先摘下来的底叶,晾在窗台上,晒干搓碎就可以抽了。这是劣等的旱烟,一般用来补缺。“上”好了“烟”的烟叶,被父母摘下来码成堆,放在仓房一角。这时山上的香蒿也成熟了,散发出浓郁的香味。哥哥们按照父母的吩咐,割回来几大捆。父母把香蒿铺在地上,把烟叶分层铺在香蒿上,一层烟叶一层香蒿,捂严实。这个过程之后,烟叶变得橙黄且有香味了,就可以用马蔺编成的绳子串起来,挂在柳条笆墙上晾晒了。也许三五天吧,某个有雾的早晨,晒干的烟叶变得柔软时,父亲或母亲就赶紧把它们从绳子上取下来,一个一个铺展好,五个八个地摞在一起,再用泡好的马蔺叶子一把一把地捆扎起来,然后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继续风干。这就是上好的旱烟了。以后还会陆续有烟叶被摘下来,以此法处理,一直到老秋。
后园子烟地西侧,通常有一小块玉米地。这是专门为初秋烀苞米吃准备的。地方小,种不了几棵,也就够吃两顿的。
房前屋后的园子加起来也不过一亩地,被父亲分割成若干个小区域之后,它简直成了百花园、百菜园、百宝园。哪里种啥,怎么种,基本由父亲说了算,我们最多是帮忙干活。
那时,我从没注意观察别人家的园子,是不是也如我家的。但从我家院墙外路过的乡邻们总会停下来往里看看。遇上有人在园子里干活,人家还会啧啧称赞几句。
那是称赞父亲的。
如果父亲还在,老家的土屋肯定不会易主——父亲的园子,也许还是从前的样子吧?
父亲的纸笸箩
在父亲的眼里,什么都是有用的。
他会随时随地把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顺手收集起来,就连走路也会不时地弯腰拾起地上的铁钉、铁丝、麻绳头,有时甚至是半张废报纸。回到家里,他把捡来的这些破烂儿分门别类存放起来。不知道什么时候,那些破破烂烂的小玩意儿,还真能派上用场。
从记事开始,我家里就有很多大大小小形状和功用都类似于盆的器皿,是纸做的,家人叫它们纸笸箩。大的有过去农村用的大号泥瓦盆那么大;小的呢,也就小碗那么大。那些纸笸箩,除了不能装液体类不能装潮湿的物品,其他的都可以装。比如盛米、盛面、装晒干了的菜、装揉碎了旱烟,甚至当针线筐、棋子盒,用途可多呢。
制作纸笸箩,工期长,工序也很繁琐。在我们村,好像只有父亲会做,或者说,只有父亲不怕麻烦,乐于制作。
首先是收集废纸,去除杂质后,浸泡在园子里的一口大缸中。这期间不换水,要让泡碎的废纸充分发酵。发酵的废纸气味难闻,我可不愿意到那大缸跟前去。
过个十天半月,也有可能是一个月的时间,等废纸泡透、泡软、充分发酵,然后从缸里捞出,放进比较结实的容器里,用铁锹把粗的木棍将其捣碎。用木棍捣过之后,如果不够碎,还要用手攥,直至成纸糊糊。
第三道工序就是制作笸箩。根据碎纸糊糊的多少,准备好米汤样的白面浆糊,将浆糊和纸糊掺和均匀,这种粘乎乎的东西就叫它纸浆吧。再找出合意的模具,将纸浆一层层拍到模具上,要厚薄均匀。做好了,就把模具倒扣在阴凉通风的地方,慢慢晾干。可不能在太阳底下暴晒,那样纸浆会因为干得太快而产生裂缝。
等模具上拍好的纸浆快干透了,就想办法撤出模具,纸笸箩就基本做好了。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,将纸笸箩里外裱糊好。旧年画、图案好看的香烟纸标等等,都可以做裱糊的材料。父亲会画水彩画,有时候也会在白纸裱糊好的纸笸箩上画一些祥云、花鸟的图案。但这是极少的,因为父亲没有那么多时间。
父亲做的纸笸箩有方有圆,有大有小,有高有矮。因为他选用的模具有时是盆,有时是木匣,有时是水桶甚至罐头瓶。如果做完了一个大笸箩,还剩下一点点纸浆,他可能会顺手拿起一只小碗做模具。这些大大小小的纸笸箩,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可算得上是我家特有的财富了。有时,串门的乡亲一边坐在炕上抽烟唠嗑,一边赞叹我家的烟笸箩好看,父亲会很大方地送人家一个。所以,村里的亲戚、朋友,很多人家都有父亲的“作品”。
纸笸箩用的年头多了,会被虫蛀,留下很多小窟窿。虫蛀过的纸笸箩就不那么结实了,极易掰裂、掉碴儿。这时,母亲会用纳鞋底的细麻绳把裂缝、掉的碴儿缝好,再重新裱糊一下,就可以继续使用了。
那时,我根本意识不到父亲做纸笸箩的手艺,就是传统手工艺,也从没珍惜过那些纸笸箩。看着它们因年深日久,变得黑黝黝的,甚至有点讨厌。随着又好看又结实还不怕水的铁漆盆、铝盆、塑料盆逐渐走进日常生活,那些浸透着父亲智慧和汗水的小物件就渐渐淡出了我的视线。
直到有那么一天,漂泊的心在繁华里疲惫,浮躁的灵魂在喧嚣中沉寂,我开始喜欢一个人独处。在氤氲的茶香里,回忆父亲的点点滴滴,触摸他平凡外表下,那不屈的性格,我才惭愧地意识到我是多么蠢笨!在我空空的行囊里,没有保存一件父亲的笔迹、手迹、作品——那是任何现代高科技都无法复制的!
好在,我的脉动里流着他的血液,我可以越来越像他……
父亲的旱烟叶
因为要用一瓶玻璃胶,去了一家平时不怎么去的小五金日杂店。店主说,得用专门的“枪”才能将胶挤出来使用。可是,这种东西不是日常用品,可能一年也用不到一两次。胶,一次就用完了,“枪”,不是一次性的,岂不有些浪费?我试着问店主:可否借用你店里的“枪”?店主倒也痛快:留下10元押金吧,一会儿用完送回来,再把押金退给你。因为这个理由,我在一小时内两次来到这家小店,事情顺利,心情也不错。所以,最后离开的时候,我特意回头看看店牌,意欲记住这家通情达理的小店。就在这一回头间,我的目光被一样东西牵扯住了。
一箱旱烟叶!
久违了的、熟悉的、亲切的旱烟叶!
我不吸烟,再高档的香烟,我也从不注目。可是,眼前这一摞装在纸箱里的旱烟叶,却让我的心暖暖的激动起来。很多亲切的往事,像早春冒芽的小草,欣喜地涌动着。
是的,我想起了那个人,那个不仅给了我生命,还给了我坚强品格的人!
我曾经在去年的一篇小文《父亲的园子》里,详细写过父亲种旱烟的事儿。种旱烟是个苦差事,一些出力气的笨活,我们兄弟姐妹能帮忙,一些细作活,可都是父母亲自动手的。尤其是用香蒿“捂”烟叶的过程,父亲一定要全程监控。捂多长时间、捂到什么成色,全得父亲说了算。还有上绳、晾晒、捆扎几道工序,也是父母动手做的,怕我们毛手毛脚做得不利索。父亲是个善于积累经验的人。所以,我常常感觉他什么都会,就像乡邻称赞的那样,是个“巧”人。在种旱烟、制旱烟的过程中,他的经验得到了验证。很多到我家串门的乡亲,都说我家的旱烟好抽,味儿香,有劲儿,不呛嗓子。
每年,仓房的木架子上,都有一、两个大纸箱旱烟叶,用马蔺叶子捆成一把一把的,橙黄橙黄的,码得整整齐齐,头尾一顺地躺在箱子里。从头一年的秋天一直到第二年的秋天,由多变少,等最后就剩下一小笸箩碎叶的时候,新的旱烟叶也就下来了。这样新的接旧的,父母从不用买烟抽。后来,有三、四个哥哥也学会了抽烟,家里的旱烟就有些紧张,不等新烟叶下来,陈烟叶就抽没了。母亲这时往往会把秋天割倒的烟秸找出来,从那上面摘些深秋没有被取下上绳的小叶。当然,那残余的烟叶颜色发暗,味道估计也不好,母亲管那“烟丫巴”。父亲说:“将就抽吧。”
父亲做事严谨认真,仅从他捆扎旱烟叶的细致上就可见一斑。有乡亲到我家来串门,一边抽烟一边还调侃父亲:“老鲁,你看看你把烟叶扎得这么板正干啥?早晚还不得揉碎了抽?”父亲和气地笑笑,不辩驳也不解释。下一年,他仍然那么做。
我离家读书、工作后,老家也分解成好几个小家,只有未婚的小弟小妹还围在父母身边。那时,父亲已经不再种那么多旱烟。等父亲走后,母亲就不种了。母亲学会了抽洋烟——香烟卷。渐渐的,老屋的旱烟味淡了,装旱烟的纸箱、纸笸箩,也都成了废品被丢弃了。等父爱在我的生命里升华为怀念,我已找不到多少可以寄托这种情感的符号……
在小五金日杂店门口,看到纸箱里的旱烟,我好不欣喜:这物件,我该有三十年没见了吧?我想买一把,可是家里没人抽烟,即便来客人,也不可能抽旱烟了。一把干干的烟叶,我要怎样保存,它才不碎呢!犹豫再三,我用手机拍了照片,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那家商店。
回眸间,心热热的,眼睛湿湿的,竟没看清店牌的名字……
父亲的缝纫机
用母亲的话说,父亲就是:看啥都是好的,有用没用都往家里倒腾。
母亲总这样唠叨,却一直在用着父亲“倒腾”来的“有用没用的东西”,唯有缝纫机例外——母亲一辈子不会用缝纫机。
其实母亲一点也不笨,她不是学不会使用缝纫机,她根本就没学。父亲把那台老旧的缝纫机“倒腾”到家里的时候,母亲刚年过半百,她认定了自己学不会,所以,连碰也不碰。
父亲“倒腾”来的缝纫机的确太老旧了,已看不出它的出厂日期。父亲说,它在我们村成衣铺里(村子当时是国营牧场,成衣铺归场部所属,是集体性质的)工作近50年了,是成衣铺里最好的裁缝师傅使用的,上海大四四牌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,成衣铺黄了,手艺最好的裁缝也举家搬迁到别处,剩下几台缝纫机闲置在空厂房里。时间久了,厂房漏雨,缝纫机淋雨后潮湿锈蚀,连台面的胶合板也被泡得翘起来。八十年代中期,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,原来集体所有的土地、牛羊牲畜、机械器材等逐渐承包、转让给了个人。那几台缝纫机也被一一作了价,等着人买。可是,那时全村会使用缝纫机的人实在不多,何况那几台缝纫机都快成了废品,根本无人问津。父亲却像发现了宝贝,看中了那台被定价为50元的上海大四四。
父亲兴高采烈地求人用毛驴车把缝纫机拿回家,跟母亲说:咱家人口多,这些年一直靠你手工缝衣做鞋,这回有了这台机器,你也能轻巧点了。再说,三丫头也会做针线活了,有了机器,她用着也方便。
母亲看了看缝纫机,鼻子哼了哼,不屑一顾地说:人家卖废铁的东西,你也花钱买回来当宝贝!
父亲受了奚落并不生气,他翻箱倒柜地找出机油、螺丝刀、毛刷、抹布等一应工具,先把缝纫机所有部件用机油擦拭一遍,然后给缝纫机上油,连螺丝钉的部位也不落下。父亲一边收拾缝纫机,一遍跟母亲说:这可是上海名牌大四四呢,真正的好东西。你别看它被雨水泡了,生了锈,台面也坏了,可是好好修一修就能用,拿普通的新机器都不换呀!母亲对父亲的话不置可否,但从她的表情上,一下子就能看出:母亲可没把这缝纫机当回事,倒是埋怨父亲乱花钱了。
父亲用半天时间,终于让缝纫机转了起来。嗡嗡嗡的声音很好听,看着父亲忙乎了一阵子,就把一台“泡病”缝纫机治好了,我满眼的敬佩。父亲也欣慰地说:这钱不白花!
接着,父亲把翘起的台面扯下去,在凸凹不平的台板上抹腻子、糊木纹纸,再用清油刷,虽然仍旧不平整,但缝纫时不至于刮布料了。
缝纫机终于能用了!父亲高兴地笑着,满脸络腮胡子茬也跟着笑容一颤一颤的,他亲自用缝纫机缝了一双鞋垫。
父亲教会了我使用缝纫机,还教我要一边用一遍保养。
不过,无论父亲怎样劝说,母亲就是不肯学缝纫机。父亲说:你妈不学就不学吧,你们几个(我和小弟、小妹)要学会,以后自己过日子不憋手。
对于父亲的那台破缝纫机,很多人跟母亲的态度相似,认为不值得花那么多钱。母亲虽然不认可那台缝纫机,却时常把一些缝补的零活给我,让我用缝纫机缝。有时她做棉衣棉被,就先把需要缝合的长缝交给我缝,然后她再铺在炕上絮棉花。
时间久了,母亲不再唠叨,可能是默认了父亲的缝纫机吧。
父亲病重时,我还是个穷光蛋,不能从经济上回报父亲一点点,只能经常回去看看,给他做点喜欢的饭菜、洗洗衣服。有一次,父亲很郑重地对我说:“这台破机器没人得意它,就你知道它的好,干脆你拿去吧。不过家里还有你小弟小妹没成家,不能白给你,多少给点钱。”我懂父亲的意思,我愿意保留父亲的这份念想。我对父亲说:这缝纫机我愿意要,我现在没能力多给钱,就给150元吧!父亲点头答应,但母亲提出反对意见:那可不行,你拿走了,你弟你妹用啥?等你弟订婚买了新的机器,你再拿走这个,先给我们用着吧!
就这样,父亲走后,缝纫机依然留在老家,小弟小妹偶尔也会用一用。我毫无怨言的等着,等着小弟成家,有了新的缝纫机用,我就可以拿走了。
在我们老家,有一句俗话:好儿不争分家饭,好女不争陪嫁衣。我算不上好女儿,因为我没能力孝顺父母。但我出嫁时,的确没要父母一分钱的陪嫁。可是父亲那台缝纫机,我真的想拥有,不是白拿,是用加倍的钱买。目的只有一个:保留一份带着父亲体温的物件,作为长久的念想!
小弟成家后,我跟小弟商量,按照父亲的遗言和与母亲的约定,想把那台破旧的缝纫机“买”过来。但小弟说弟妹要用,多少钱也不“卖”给我了。
既然弟和弟妹也愿意保留父亲的遗物,我还能说什么呢。
后来,我自己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,正是孩子小、日子紧巴的时候,缝缝补补地没少用,就是觉得不如父亲的缝纫机好用。零九年搬家时因为路途远不方便带,我把它100元转给了亲戚。
本想不再用缝纫机了,可经不住心里痒痒,去年淘回了一台北京牌旧缝纫机,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物件。看着它,布满沧桑的回忆便暖暖地在心里流淌。闲暇时,找来旧衣改兜子、旧裤改马甲、缝个床单被罩、坐垫鞋垫啥地,别有乐趣。
但是,还是觉得不如父亲捡回的那台破旧缝纫机好用。
父亲的小发明
前段时间给婆婆陪床时,临床一位姓冷的八旬退休老干部跟我聊天,问我家乡姓氏,然后问我父亲是否健在。我说他老人家已经走了二十多年了。他无限感慨地说:我认识你父亲,那人可好。
父亲若健在,九十多岁了,比那老者年长十多岁。想来当年他们相识的时候,那老者该是风华正茂吧?一个风华正茂的国家干部,能给一个普通百姓这样高的评价,不容易。
在他赞扬的话语里,我自豪地回想着父亲:音容笑貌、举手投足、勤劳品质、聪明才智……不知不觉就想到了父亲的小发明、小制作。
父亲不仅勤勉自律、为人厚道,而且心灵手巧。这表现在他画画、糊棚、做纸活、养花种菜样样都做得很好,也表现在他总爱鼓捣一些小物件,做些小发明。这些小发明,有的灵巧,有的笨拙,但都很实用。
比如“卷烟机”,有轴有箱,完全木制,小巧灵活。具体的结构我已记不清了,只依稀记得父母经常把自家种的旱烟叶用剪刀剪碎,装入卷烟机,稍稍转动细木轴,一根粗细均匀、比香烟杆略长的烟卷就出来了。然后将烟卷的纸边蘸一点米汤粘好,晾干后就可以招待客人了。要是自己吸的话,干脆就用吐沫粘上。
再说“捣碎机”吧,就是把一节手腕粗的竹筒锯开,另一头利用竹节自然的封堵,做成一个敞口有底的筒子,再把一根比格尺厚点的木条的一头嵌上刀片。这个组合看起来简单至极,却方便实用。把干辣椒放进筒子里,用带有刀片的木条轻轻捣,片刻,干辣椒就变成了辣椒末,连辣椒糊辣椒籽都在里面,一点也不浪费。因为竹筒细长,捣的时候,辣椒碎末不会飞溅上来,也不会辣到眼睛;而且辣椒易集中,碎得特别快。亲戚、乡邻们也经常借用。记得父亲还用它捣过从野外采回来的山花椒,那味道,比现在超市里买的花椒味道浓得多。
要说那个“压菜机”实在笨重,是父亲专门为减轻母亲的劳动量做的。我家人口多,穷日子里吃野菜的时间很长。挖野菜、摘野菜劳动量虽然大,却不单单是手腕用力。但把焯好的野菜攥干时,完全靠臂力、腕力,时间长了,母亲的胳肢窝就起了裸肋疙瘩,胳膊也经常红肿抬不动。那时我的哥哥姐姐们大都在上学,我和弟弟小,妹妹还没出生,攥菜这项看似简单实则强度很大的劳动,没人能帮母亲。父亲就起早贪黑赶做了一个特殊的装置:用烧红的铁棍把四块木板烙出很多筷子粗细、分布均匀的小孔儿,然后以卯榫的方式将四块带孔儿的木板围成个正方形的木框,高不足1尺,长1尺有余。另外还有一个能摘下能挂上的类似于杠杆似的木棍。攥菜时,在12印大铁锅上横放一块木板,把那个四面带孔的木框放在木板上面,再把要攥的菜捞到木框里,用盖帘盖好菜,盖帘上放一块大小合适的重物,挂上那个起杠杆作用的木棍,木棍的另一端朝向不碍事的地方,再挂上一桶水。这时,焯好的野菜里的水分就被挤压出来,从木框四面的孔眼流到锅里。母亲呢,自然是不用站在那儿等菜压干,可以去忙别的事。等到快要做饭的时候,野菜已经被挤压干了,比手攥的还干呢。这个看似笨拙的装置,帮了母亲很大的忙。邻居舅妈们来串门,看到这一幕,都羡慕地说母亲真有福,摊上个手巧又知道疼人的老爷们儿。
等到我长大会做饭的时候,家里已经不再靠野菜度日了。所以,父亲的“压菜机”我一次都没用过。我记得那些木框、木板之类的装置,在西仓房闲置了很久。卯榫虽然没有松动,但上面挂满了蜘蛛网和灰尘。我有时去仓房拿东西,不经意间会看到它们,仿佛被哪个朝代遗忘的贤达名士,独自坐在角落里沉默着,等着再度被启用。至于具体什么时候被清理掉的,我就不清楚了。
现在,吃野菜像过去吃燕窝鱼翅那么难,偶尔弄来一点点,一把两把就攥完了,哪儿还用得着什么“压菜机”?可是每次攥菜的时候,我还真就会想到父亲那个笨拙的压菜装置,由衷地钦佩父亲好男人、大丈夫的胸怀和品德。
磁性的爱
今天我过生日。
早晨照常起来做饭,我身边的两个男人照常睡觉。
一边忙碌,一边暗自思忖:这个生日与往年的一样,没有人记得。
六点半,做好了饭菜,叫小男人起床——大男人不用叫,听到我招呼小男人,自己就起来了,比小男人强多了。
招呼了小男人三遍,终于懒洋洋地起来,一边穿衣服,一边说了一句:“妈妈生日快乐!”我惊喜:原来小男人记得我的生日!
趁他们上厕所、洗漱的时候,我端上饭菜,坐在那儿等他们上桌。今天没做什么特别的饭菜,用炒勺炖茄子土豆,给小男人加了几块瘦肉;炖菜上面贴了一圈小馒头。这道饭菜,有点像农家饭庄里的“农家一锅出”,是一家人都爱吃的。另外煮了六枚咸鸡蛋,算是给生日一个特别的点缀——不是舍不得煮鸡蛋,主要是除了我自己,两个男人都不爱吃煮鸡蛋,就是咸鸡蛋吧,还勉强。
小男人洗漱完,走进卧室又很快出来,到我身边说:“妈妈,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。”我愈发惊讶:“怎么?还有礼物?”“嗯,是一对磁性耳钉。”一边说着,一边给我戴上。我走到镜子前,看到耳朵上一对晶莹闪亮的银色耳钉,挺漂亮。
我顿时一阵感动,禁不住泪盈眼眶,拥抱了小男人一下。
我出生的时候,父母已经有了五男二女七个孩子,被生活累得精疲力尽。虽然我是女孩,也未享受到太多的关注。老家有个风俗,女孩出生后三天,就请接生婆给扎耳眼。据说,新生儿时期扎的耳眼儿,一辈子都不会愈合长死。母亲生我的这个时候,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季节。母亲坐月子连像样的饭都吃不上,哪有闲心顾得给我扎耳眼儿?
好在娶我的大男人当时也很穷,没送我耳环、项链、戒指之类的饰品,我没有耳眼儿也没觉得尴尬。
小男人快一周岁的时候,外甥女娟陪我去附近的小店理发,看到美发店正搞清明节打耳眼优惠活动,就鼓动我打一个。理发师也撺掇说:“你的耳朵有点朝后抿,戴个耳环之类的饰品应该能弥补不足。现在是清明节期间,打耳眼儿不发炎。”那时,虽然日子过得清贫如洗,但女人爱美之心未泯,我到底没经住鼓动,就打了一对耳眼儿。
打了耳眼儿,却没有像样的耳环。担心那种廉价的饰品会导致耳眼儿发炎,我也就一直没戴什么。后来,外甥女艳给我买了一对银耳环,可没戴多久,就丢了一只。
几年后,突然有一天发现,我的耳眼儿已经愈合了,原来的针眼位置结出了一个小小的硬结。
耳眼儿长死了,就更没有戴耳环的心思了。
一天晚饭后无事闲聊,小男人摸着我的耳朵问:“妈妈,你怎么不戴耳环?”
我说:“耳朵眼儿都长死了,还戴啥。”
他说:“有那种两面都是磁性的,夹在耳朵上,就能相互吸着,像耳钉一样。”
我当时并没在意他的话。谁知,听者无意,说者有心了。
戴着小男人给我买的耳钉吃饭,心里美滋滋的:这臭小子,看着像一头小倔驴,竟然还这么细心呢!
我忽然想起什么,便问到:“儿子,你咋会有钱给妈妈买耳钉啊?”小男人平静地说:“我晚饭简单吃了,只花4元钱,省下6元钱买了耳钉。”
我无语,眼睛有些潮湿。这耳钉的价值,已不能用钱多钱少来衡量了。
小男人坐在我对面,边吃饭边得意地看着我。饭后,小男人匆匆上学走了。
大男人今天休息,很自觉地帮我收拾碗筷。
房间收拾停当,我去楼下倒了一次垃圾。回到屋里,想把耳钉取下来,然后洗头。伸手一摸,心里就是一惊:坏了!怎么两只耳朵都光光的,耳钉呢?东西虽然不值钱,可心情无价啊!我低头在室内四处搜寻,希望一瞬间发现那两枚或四枚亮晶晶的小颗粒。可是找遍了所有的犄角旮旯,也没有找到。我想,也许是下楼倒垃圾时丢了。于是沿着楼梯仔细看了一遍,仍无所获。回到屋里,失望之余,不免有些奇怪:虽说耳钉不大,可地板又没有裂缝,掉在地上也应该能找到啊!
无意间瞥见大男人正得意地坏笑,看我狠狠地盯着他,便故意问:“找啥呢?”
“儿子刚才送我的耳钉,掉了,你看见没?”
他迟疑了一下,大概想说没看见,但见我真的很着急,就笑着伸开右手说:“喏,我从地上捡到的。”
我心中的焦急和沮丧一下子烟消云散,小心翼翼地用面巾纸把耳钉擦拭干净,收到首饰袋里——这对磁性耳钉是小男人长大、懂事的证据,戴在耳朵上,也许会丢了,不如戴在心里吧。
亲情是有磁性的呢。
白雪铺路,为姨妈送行!
清晨,电话铃突然响起。这么早打电话,一定是急事。我赶紧拿起手机,看来电显示是“国新大哥”,我的心猛地一沉:那个最怕听到、却注定早一天晚一天都要听到的噩耗,来了!果然,国新大哥深沉地声音印证了我的猜测:老太太走了,今天早晨……
国新大哥是老姨的大儿子,他说的老太太,是我的老姨,母亲四姊妹中最小的妹妹,也是母亲四姊妹中最有知识、唯一的国家干部。如果按照天增一岁、地增一岁的习俗算,老姨享年80岁。
放下电话,起床拉开窗帘,见外面正飘着小雪,地面已被覆盖。原来,苍天知道老姨今天归去,早已用白雪为她铺好了路——是的,老姨勤勉一生,慈善一生,仁义一生,是该享受这样的待遇!
眼泪和雪花一样,无声地、碎碎地落下。我将迷蒙的双眼望向遥远的苍穹,仿佛又看到老姨慈祥的笑脸,听到她爽朗的笑声。脑海中,忆起我所知道的老姨的点点滴滴。
老姨年轻时是村里屈指可数的美人儿,又有知识又有工作,令很多人羡慕。外祖父母也对老姨期望很高。可老姨偏偏嫁给了一个家有老母、还带着两个孩子的丧偶同事,遭到外祖父母的反对。因为这在农村传统观念里叫做“填房”,好好的大姑娘去做“填房”,是要被人耻笑的,但我父亲支持。父亲说,找对象是给自己找,自己看着合适就行。
老姨和老姨父的感情虽然很好,但老姨婚后的日子却很累。她这辈子,一直都在为别人活着。
老姨帮着姨父把前妻留下的两个女儿抚养成人,并且都为她们找到了工作成了家。老姨自己生了二男三女五个孩子。老姨一边上班,一边上敬老、下养小,艰苦的日子过了半辈子。刚刚要好转,小儿子就得了医学上称之为疑难病症的“肌肉萎缩症”。上海、北京、天津、沈阳等大城市都跑遍了。实在不行,老姨就求神问卜,找巫医大仙儿,总之是想尽了一切办法。总算苍天有眼,保住了小儿子的命,但是身体严重变形,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儿,弯腰曲背像个小老头儿。不久,姨父又脑血栓瘫痪在床。老姨悉心侍奉姨父的十几年里,大孙子又得了严重的肾病。这一老一少一小三个重病号,让老姨心力憔悴。十几年前,姨父瘫痪16年后撒手而去。老姨将全部精力放到孙子和小儿子的身上。谁知,六年前小儿子又突发脑出血离世。那时,我非常担心老姨会受不了打击……但是,老姨挺过来了!她说:“还有别的儿女需要我,特别是我老儿子的闺女,更需要我……为他们,我得好好活下去啊!”
在母亲走后近20年的时间里,我常常把老姨当成妈,和她唠家常、说心事、诉委屈。老姨也像疼闺女一样疼我,大事小情都想着我。
四年前,身体一直不好的老姨,检查出了肺癌,是晚期。老姨的儿女们及其孝顺,对老姨隐瞒了病情。老姨退休前一直在医药公司上班,精通业务。要对这样一位聪明的老人隐瞒病情,何其难?但老姨的儿女们做到了。每次去大医院、小医院看病,都要提前和医生沟通好,还要将所用的药品全部换了包装。老姨就在儿女们善意的谎言里配合治疗,积极、乐观地活过着,远远打破医生断言的半年预期。
知道老姨患病后,我尽可能多地去看望老姨。但是,每次迈进门槛那一刻,我又想快点离开。因为看着老姨被病痛折磨,我的心就揪着疼。那种无法替代、无力解救、又不得不面对的疼,不但不能说,还得强装轻松。
每一次离开老姨的家,我都清楚地知道:我和老姨见面的日子又少了一次!我明白老姨在世时日不多,担心她突然离去,却又希望她早日从剧烈的病痛中得到解脱——这种矛盾的心情,是至亲骨肉才有的感觉。
老姨一生为人谦和友善,众多的亲戚朋友,没有不称赞的。我相信,老姨离去的日子里,一定有很多人怀念她,不仅是她的儿女们,亲戚们,朋友们,还有她的邻居们。
无论这个世界多美,人总要离开。倘若能在离开之后还有很多人怀念,那他(她)的这一辈子,就没白活。
外面的雪花越飘越多,远处的山川、田野都披上了圣洁的银装。大地没有了黑暗,路面没有了坎坷——老姨,天堂的路光洁如银,您放心去吧,那里一定没有疼痛,没有苦难!
我收回思绪,擦干眼泪,穿衣戴帽,决定去送老姨一程。此时她老人家已安睡,我不再担心看到她被病痛折磨而心难受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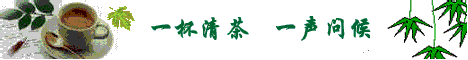
 最新评论
最新评论